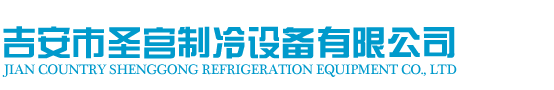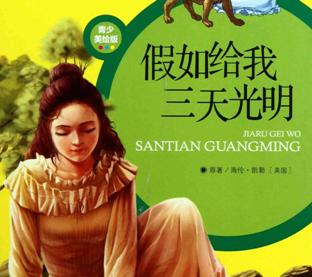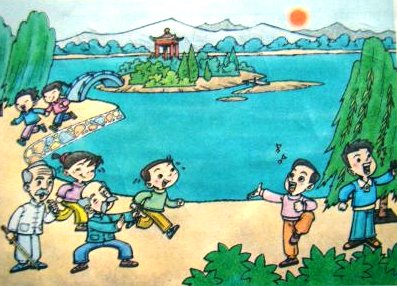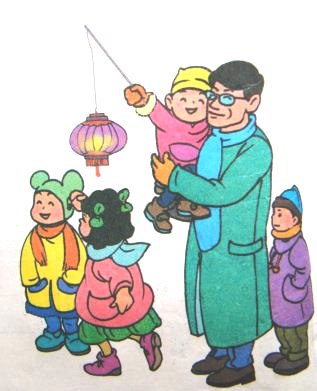和你一起學作文-語言:“永遠變化無窮”
對寫作來說,語言是最重要的基礎。具備一定程度的語言表達能力,是作文最起碼的要求;而要寫出好文章,就必須在語言方面精益求精。
關于語言,我想和同學們談五個問題。
一、要細心體會漢語“變化無窮”的魅力
魯迅說:“牌有怎樣的有趣呢?我是外行,不大明白。但聽得愛賭的人說,它妙在一張一張地摸起來,永遠變化無窮。我想,凡嗜好的讀書,能夠手不釋卷的原因也就是這樣。”這位賭徒頗有意思,他竟把賭的樂趣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。而在“變化無窮”這一點上,倒也的確是與讀書寫作的樂趣相通的。
“文似看山不喜平”,“平”就是靜止,就是趨同,就是沒有變化。而文章只有在變化和發展中,才有可能體現出作者的個性和創造力。其實在這方面,漢語是為我們提供了很大的用武之地的。漢語,因其建構的簡易性和組織方式的靈活性,因其詞語活動的能量大,彈性也大,可以更好地體現立言造句的主體意識,這就為語詞運用的藝術化提供了更大的余地,使寫作者可以更好地活用,閱讀者可以更好地聯想,由此則可以產生“豐富瑰麗的藝術效果”。
讓我們來看一個充分顯示漢語用字精練而內涵豐富的例子吧。杜甫的《登高》中有這樣兩句詩:“萬里悲秋常作客,百年多病獨登臺”。古人說這十四個字當中有九層“悲”的含義:“作客”即在外漂泊,不能安居,此其一;“常”即經常如此,此其二;時值深“秋”,一片蕭瑟,此其三;地則偏遠,家在“萬里”之外,此其四;人生不過“百年”,我今老矣,此其五;又有“病”,此其六;且“多”病,此其七;今日重陽“登”高,尤覺凄涼,此其八;何況又是一人“獨”登,豈不更加傷悲,此其九也!區區十四字,盡是單音詞和雙音詞,用字極簡,組合極易,而內蘊竟如此豐富,氣氛竟如此沉郁。不好好分析聯想,又怎能充分欣賞呢!
如此精妙的用詞造句,在古典小說中也是很多的。金圣嘆在評點《水滸傳》時,就有不少精到的分析。如下面一段對魯智深的描寫:“智深吐了一回,扒上禪床,解下絳,把直裰帶子都必必剝剝扯斷了,脫下那腳狗腿來。”金圣嘆評道:“‘取’出來便是俗筆,今云‘脫’下,寫醉人節節忘廢入妙。”確實,這個地方用“脫下”,似乎不合常理,且違背語法,然而卻生動地表現出魯智深酒醉后的神態,這正說明了漢語句法的變化無窮,正如清人沈德潛所說,是“以意運法”的“活法”,而不是“以意從法”的“死法”。讓我們再看一段對魯智深的描寫,其中加括號的是金圣嘆的評語:“太公道:‘師父請吃些晚飯,不知肯吃葷腥也不。’(著,然只問葷腥,卻偏不問酒,妙筆。)魯智深道:‘灑家不忌葷酒(自增出一酒字,妙筆。)遮莫什么渾清白酒都不揀選(反先說酒),牛肉狗肉,但有便吃(次補肉)。”這看上去只是一段文字淺顯的對白,可這里面有多少絕妙的潛臺詞,有多少微妙的心理活動啊!如果沒有金圣嘆的評點,我們會不會囫圇吞棗地一讀而過呢?
同樣,在語言大師魯迅的作品中,我們也經常會讀到令人拍案叫絕的詞語活用。“我到此快要一個月了,懶在一所三層樓上。”這個“懶”字在這里作動詞,用法新奇,出人意外,傳達出魯迅當時孤寂落寞的心情。這是一個以少勝多的例子,下面再舉一個以多勝少的例子。“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。趕開,又來;趕開,又來;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。”現在讓我們仔細來體會一下:連用三個“爬”字,是不是好像產生了一種“癢爬爬”的感覺?兩個“趕開,又來”的重復,是不是活現出極不耐煩的心情?再用兩個“一定”的隔離反復,最后再重復一個“爬”字,則完全是一種無可奈何、哭笑不得的口吻了。經過這樣一種句式和音韻的強調,我們自然會得到一種極其強烈的心理暗示,那就是對蒼蠅的厭惡、厭煩乃至深惡痛絕。現在,如果讓我們再來朗讀這段文字,我們該知道怎樣來處理其語調、重音和節奏了吧!
接著我們就來談談語言節奏的奧妙。所謂語言節奏,指的是語言運用中有規律的強弱和長短的現象。語言節奏的變化,往往在文章中起著重要的作用。
你讀過捷克民族英雄伏契克的《二六七號牢房》(節選自他的《絞刑架下的報告》一書)嗎?文章開頭是這樣兩句話:“從門到窗子是七步,從窗子到門是七步。”這兩句話的句式完全一樣,只是把“門”和“窗子”對調了一下,就把作者在窄小的牢房中來回踱步的情景和心理生動地描繪出來了。這是一種單調乏味的、無數次重復的走來走去,顯現出獄中那種沉悶孤寂的氣氛和作者渴望自由而不得的煩躁心情。如果把它改成“我在窄小的牢房里反復地來回踱步”,就遠不如現在這樣含蓄而意味深長了。
前蘇聯作家戈爾巴朵夫有一部反映衛國戰爭的長篇小說《不屈的人們》,那著名的開頭寫道:“全是往東去,全是往東去,哪怕有一輛往西去的也好!”為什么說這個開頭好呢?因為當時是德國侵略軍發動突然襲擊的“閃電戰”,從西往東大舉進攻,而蘇聯紅軍猝不及防,一時間兵敗如山倒,然后就不得不開始了向東方的大撤退。當時蘇聯人民的心情,是盼望著紅軍早一點開始反攻,從東向西打過去。所以說,這個開頭一下子就把蘇聯人民那種焦急、盼望的心情和盤托出,為整部小說奠定了基調。
有一篇散文《荷葉詠》是這樣開頭的:“陣陣沁人心脾的清香從河上飄來,愈往前走便愈分明地看出湖上的那一片墨綠。啊,到了,荷花洲!”作者先從嗅覺上寫聞到了從荷花洲上飄來的清香;再從視覺上寫看到了“那一片墨綠”,開始還比較遠,所以看不分明,愈走便愈分明;下面就在語言節奏上做文章了:“啊,到了,荷花洲!”這是三個獨詞句,巧妙的是一個字、兩個字、三個字的排列,給讀者帶來荷花洲越來越近、越來越大的感覺,多像電影當中在往前推鏡頭啊!
在詩歌當中,語言的節奏就更加重要,我想就不用再舉例了。